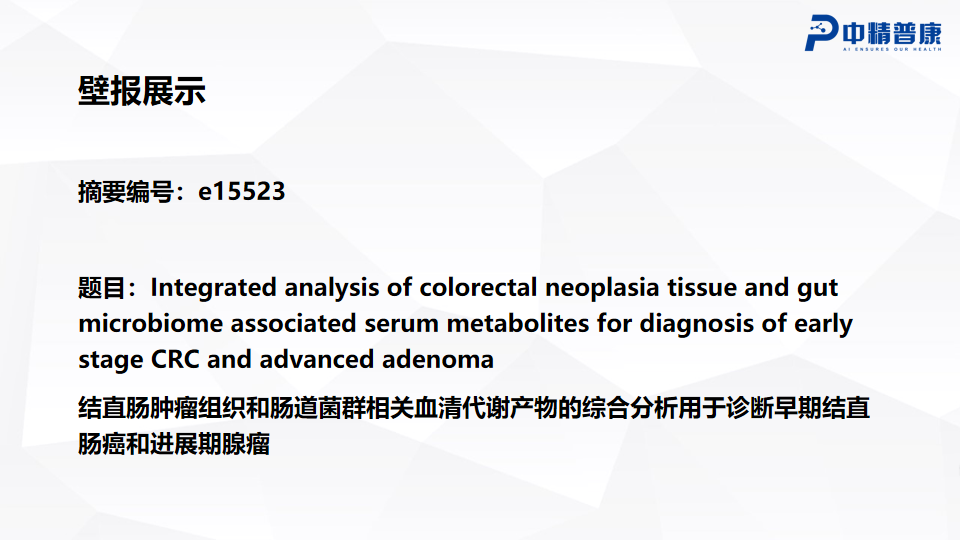对万玛才旦的慎重情感
◎巫昂(作家)
5月8日下午,多方信源证实,中国藏族艺术家万玛才旦当日凌晨逝世于西藏,享年53岁。
 (资料图)
(资料图)
万玛才旦,1969年12月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中国著名导演、编剧、作家、制作人。
今年3月底,万玛才旦自编自导的新片《陌生人》刚刚拍摄完成,目前正在后期制作阶段。7日傍晚五点多,万玛才旦还发了新的朋友圈——配图是藏族导演格杰白玛电影《礼物》的海报和获奖证书,“祝贺年轻的电影人!”这是万玛才旦留给世间最后的祝福。
自2005年自编自导《静静的嘛呢石》始,万玛才旦就是国内最活跃的藏地导演,持续贡献了《塔洛》《撞死一只羊》《气球》等以藏区为背景的电影。除了作为导演、编剧持续创作,万玛才旦也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坚持小说创作,去年才出版了新的短篇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
相较于个人创作成就,万玛才旦对藏地电影甚至中国电影更大的贡献是,激励并引导了一批藏族年轻人走上电影创作的道路。他是《扎旺的雨靴》和《一个和四个》的制片人和监制,他带领拉加华、久美成列、金巴等一批藏区青年电影人一起,掀起“藏地新浪潮”。
早上五点五十七分,我起床,取了一杯温水,径直在书桌前坐下打开电脑。二十几年间,我残存的写字阵地居然是“逝者”栏目,写的居然是我以为可以再活四五十年、拍出伯格曼那么长的电影清单、写出比卡佛更多得多的短篇小说的人。 ——巫昂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我们的往来之初,是2021年年底,大屏幕上《撞死了一只羊》的藏族男人变成了加了微信的亲切的朋友。我给他寄了我当时新出的书,三天后他回复“书收到了,回去拜读!”这是一个周全而忙碌的人,当时我有一个基本印象。又过了半年左右,他让我给他地址,要让出版社给我寄他新出的书,那应该就是他在中信大方出的《故事只讲了一半》,一本新的短篇小说集。此前我已经读过了《乌金的牙齿》。
过了一个月左右,他在夜里十点多跟我说:“今晚听了您讲卡佛,挺有收获的。”那是我在新浪连麦的栏目“巫聊”的第一期。讲了两期卡佛,我在连麦的嘉宾席上确实赫然看到了他的名字,一晚上静静地挂在那里。于是有了一段关于卡佛的交谈,他还知道我有个写作班,我接下来那周还要讲卡佛,他居然又如约来听,还是安安静静地在嘉宾席上坐着。那期间,我们还聊了电影与小说,写小说对于拍电影有好处等话题,像两个认真的人在聊认真的事。第二天,我就开始读《故事只讲了一半》。
万玛才旦是个怎样的人呢?连日来朋友圈刷屏的他变成了逝者的消息,人们往往说他儒雅温厚。有一位朋友说他的周全和礼貌,让他过于内耗了。他有着作为导演来说过于俊美的容颜,做演员也丝毫不差,他在任何场合出现的照片都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观者如是,我也并不例外。我们因着他所喜爱的作家卡佛开始的往复微信里,充满了他的温暖与温情。
我通常都有将喜欢的作家的书尽数收集齐的习惯。当我读了一多半《故事只讲了一半》,跟他说打算收集齐他的书,他竟然说要寄给我。因为家中几个小说集重复的比较多,朴素的理由。这是让人十分惊诧的周全,我隐约觉得这会耗费他非常多的心神。即便作为一位小说家,他的小说里有一种哈金或者说卡佛式的朴素的冷幽默。
接下来,我度过了全面了解万玛才旦作品的一个月。读完了差不多能找到的他的所有的小说,看完了他所有的电影。周全如他,电影的所有链接都是他挨个儿发给我的。
大昭寺浩浩荡荡的酥油灯
家里来了客人睡在我床上,我与母亲同睡。所以,暂时没有一个被窝,甚至一个卫生间可以掩盖我的哀恸。事实上,过去的七十二小时,我但凡不工作、不与人交谈,眼泪便充满了眼眶。需要每隔几个小时便痛哭一场,才能维续下一时段具体的生活。爱他的普通人如我也未能免俗,死,是永远必须去相信的生者自身提前的死讯。我的心从今往后将永远缺失一块,且没有酥油灯的光亮照耀。他的死撞死了我的生。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不仅仅写他之于中国电影、中国小说的不可或缺的关系的宏大叙事。我想说,这里面最大的遗憾是,一位天才创作者、一位真诚质朴而又无比丰富的人,经过漫长的岁月,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时间,然而天地不仁。
他的电影和小说都不仅仅属于这个国度,他这个人更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一位真正的作者导演的典范。自己会写小说写原创剧本,自己有着执拗而又深入的视觉和哲学思考。《寻找智美更登》里那位终于放下执念的女孩,还有《气球》中也终于放过了自己的女孩,让他拥有了不只是男性的视角。无疑,他人格中的温暖和温情,造就了这种对于电影中人的提醒和劝告。
从读完、看完他所有小说和电影之后的2022年5月底,我们就相约做一次有意思的对谈,在新浪微博连麦,那是“巫聊”的第五期(之后便停更至今)。我自己当即设计了海报,跟他约了时间,是6月17日。
与此同时,他看到我朋友圈在写一个小说叫作《跟别人的男朋友一起逛公园》。我说为此逛到了第二个别人的男朋友了,他问我这个小说写完了没有,让我写完了给他看看,原话是——“做个洪尚秀式的文艺电影应该不错”。于是,在卡佛和哈金之外,我们达成了第三个一致,都喜欢洪尚秀的电影。他对我这个小说的期待是:“故事有趣一点,能涉及两性关系的一些深层问题就好”。那段时间,我们聊过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因为他读了我的另外一个短篇《战马希恩》。我们都认为写小说是需要创新的,要有一种带着形式和美的活力。
惊人的深刻和勇敢
他的《故事只讲了一半》那本短篇集子里,我最喜欢的是《水果硬糖》。那里面也有一位非常独特、迷人的女性角色——那位老母亲。她的爱超过了对于是非的判断,她有一种对于爱的超越然而天然自得的认识与实践。他说自己也是最喜欢这一篇,还想着要有一天把它改编成电影。当时我畅想着去拉萨看这部电影,走出影院的时刻,大昭寺迎来它的晚课——一定有这种情境,那些酥油灯为了死去的亡灵超度;一定没有那种预知,一年不到之后,它要为《水果硬糖》的父亲而燃起。
我替他高兴,多么幸福啊,把自己在一本书中最喜爱的篇目,在大屏幕上再演绎一遍。我替他构思,永远不存在的那个假定性未来的某一天,他会不会自己去包个独自一人的下午场,在黑暗中对着那位老母亲永不变更的爱落泪。
另一个他的电影中我时常会想起的场景是《老狗》的结尾。所谓“老狗”是藏獒,一度是内地豪富们怀钱不遇的“奇货”,但是对于片中藏地小镇上的那位老者,他的藏獒是他的亲人。有人想方设法要盗走这条老狗,变成他们获利的商品。老者最终决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又是下午),亲自将老狗带到荒僻的草原上,将它亲手勒死。
万玛才旦在跟我的对谈中,也特地谈起了这场戏。这部电影是顺时间拍摄的,整个剧组都不知道结局如是。那天拍完,大家集体陷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压抑之中。这让我想起了史蒂芬·金小说改编的电影《雾》,那个被雾中怪物一路追赶的男人,最终选择了亲自用枪击毙了妻儿。因为深切的爱与深刻的亲密,终结所爱者的生命,免其落入其他人或者怪物之手,遭到最不堪的凌辱。这里面有一种极大、极残忍的悖论在,一种自我残忍。老狗死去后老者的存在状态,和那位击毙妻儿的中年男人一样,将要犹如丧家之犬,余生都要在难以入眠的煎熬中度过。
这场戏,让我感受到了万玛才旦惊人的深刻和勇敢。在他猝然离世后,诸君的怀念文章里都提到了他的知识分子气质,我觉得这场戏,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知识分子式的深切思考和体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到了万玛才旦这里,延伸到了“老吾老以及老之狗”,万物有灵何况老狗。
那个静穆空旷的藏地草场的下午,我想象着本来如度假一样轻松拍戏的剧组诸君,在猎猎的风中沉默不语;我想象坐在监控屏前沉默不语的万玛,我想象他那一刻的缄默犹如他之于那片土地、那片高远天空的缄默,那些他无法用言语、文字和画面说出来的无穷无尽的话,那些画外的大音希声。
所有擦肩而过的那些时间
从对谈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跟万玛才旦的见面之约,约着要好好聊聊天,预计无外乎电影和文学吧。我忍着无边无际的伤心翻看我们约见而又擦肩而过的那些时间——
2022年的7月,我到了杭州,他在次日跟我说:“到杭州了吗?我刚到拉萨。”那是疫情还未完结的时间,我本来要去天津参加芒种诗歌节,结果临了取消了,我便盘桓于杭州。
当月月底他要去First影展,问我是不是有时间,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我本来想那段时间去甘肃柳园做下一个长篇的调研,查了查地理方位,离西宁已经很近了,从敦煌飞到西宁的曹家堡机场,机票不过五百来块。
这之后他在北京的时候我在台州,我预告说9月份之后会有半年在北京,他便说那就在北京见吧。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在不同的地点,我大概也是如此,所以,能对得上的时间很稀罕。
转眼到了11月,北方的深秋,长三角的初秋,桂花已经开败了,我重新回到台州做宿写作中心的线下写作营。也在这期间,专门拿了一个下午(又又是下午),来给学生们精读分析他的电影《塔洛》。那一片黑白的下午,竟然属于一位有着小辫子会背诵《为人民服务》的牧羊人塔洛。羊走到了人间,羊迷失于人的陷阱,然后羊打算回到羊群里,然而羊已经不是羊了。羊最终被人宰杀,羊的血流在人同样踏足的地上,这就是塔洛的故事。
这是不是万玛才旦自身命运的隐喻呢?我不敢贸然下此结论,因为他不是迷途的羔羊,他更像是一位摩西——一位带领着藏地电影人和藏地电影突出重围,试图发出属于藏语和藏地景象的声音的那位有着悦耳神性的藏族名字的摩西。我用了这么多“的”,仅仅是想让他的声音在我身边再盘旋一会儿。他那种悦耳和他那种柔和、他那种温良和他那种广阔和他那种迷人,我用了这么多的“和”,仅仅因为他有那么多美德、品质、天赋、操守、爱意,一两个“和”无法概括。我用了那么多顿号,仅仅因为我已失去了巴别塔造就让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分隔的语言,我和全体的我们一样,已永失、痛失所爱。
2023年5月12日,北京东坝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