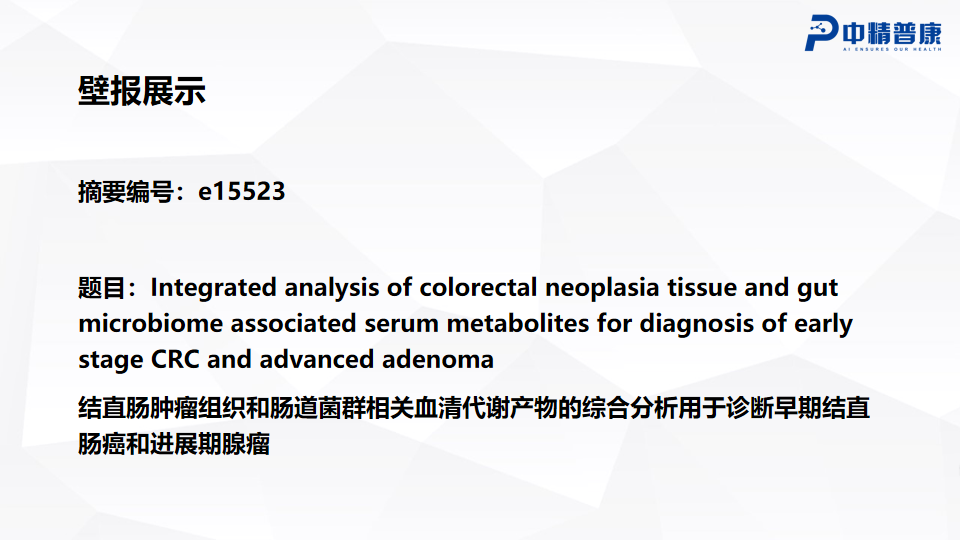【全球热闻】看,那个长翅膀的人
周六的晚上,我坐进剧场看戏。北京今春来得迟,不但春风不暖,入夜更加凛凉。台上是尘烟漫卷的流放地,我大睁着眼,见卡夫卡逡巡其间,时隐时现。至第二幕,观众席里一声长长的呵欠,不算响亮,却惊心动魄,雷霆万钧。军官即将自戕,演员浑身湿透,庞大的机器横亘于我他。
“要公正!”他吼道。随后他爬上去。他死了。
我是先读小说,再读剧本,最终看戏。这一部《在流放地》,是将卡夫卡的一角,化添出一个浑圆。对观众来说,它绝非欢乐之旅,倒像是一场质诘或自白——灵魂的非难。如果你看了,感到痛苦,困惑,毫无出路,那也许是因为这世间正是如此:痛苦,困惑,毫无出路。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在流放地》剧照(大华城市艺术表演中心供图)
和卡夫卡的小说原著对照,剧作的呈现无疑大大增添了帧率。流放地里残酷的黑白灰,跃升为饱和色彩。那庞大的刑具,荒诞的权力机器,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在轰隆巨响中驶上舞台,闯进眼里。那一刻所有无形的恐惧都成为眼前现实,叫人无法不凝望。人瞬间渺小了,连同军官一起。他参与建造了这怪物,或说信仰。他亦死在这怪物之上——或说信仰。读小说,文字如大河从眼前流过,而舞台,赋予一整个世界。
小说与话剧,确是两种艺术。同一个内容基底,感悟和理解却十分两样。之前读小说,感到人物是狂热的,坚信的,连自绝也是狰狞的。但看了戏,却感到人物的狂热之下原是孤独,坚信之下竟是疲惫。无望早已发生了。
人们在请旅行者见证的,不是一场争端,而是溺水者吐出的最后一个气泡,是一场结束。作为旅行者的堕天使,并没能真正在军官和新司令官眼中建立起权威。二人对他的争夺,只是无望者对希望的渴盼——他们知道他不是希望,他们希望他是希望。
可惜之处,是看出仓促。仓促就使人感觉,该有处都有了,但总差一口气。几位演员真的值得赞赏,把自己用到头儿,一点不留。但戏段冷热错落,长长的自白,久久的不语,实在难为演员。这样一部剧本,对表演是巨大又坎坷的考验。而台上的几位青年,让人看到了卡夫卡角色的最大可能。这部戏的流动,并非由故事或情节承启,而是倚靠在内部的哲思逻辑。若非对卡夫卡的小说有足够理解、对剧作意图有强大把握,是绝对站不到这台上去的。狂热的军官(王怡霖饰),玩笑的堕天使(徐启旭饰),敏感失落的新司令官(侯晓饰),童心可爱的小兵(康启轩饰)……每一位演员,每一位,都献祭一般投身在了这舞台,投身去了卡夫卡的荒诞世界。它便也要求观众打起万分的精神,要调动不止一双眼一对耳,还有心脑与灵魂,去一同进入那世界。
可惜,我见到了这戏剧的坚硬冷峻。它不为观众提供一个美梦,更不是一个温暖怀抱。于是发生了那长长的呵欠——未能与舞台签订契约的观众感到困倦。我想这其中原因许有多种,但必不在演员。很期待未来节奏的完善和新的排演。
最后一场戏在我看来尤为不足。堕天使与新司令官两人的交谈已经近乎轮替讲演,似乎超出了“非舞台不可”的范畴。其中许多语句,例如“人人都在流放地”,该是观戏者的感悟评论,实不该成为戏本身,由演员口说出。我是写小说的人,因此尤其在乎。小说只做小说分内的事,舞台也该是一样。
而最令神经兴奋的段落,无疑是堕天使与新司令官的思辨交换。两人常常问非所答、自说自话,却正是所言及意,乱中见序。台词赤裸刚健,清正有力。如一把宽刀,直入体躯。这里又要提起演员的功劳——不会有太多演员有能力撑得起这部戏,我由衷希望他们为自己感到自豪。
剧作对于小说最大的改编,便是将“旅行者”——流放地唯一的外来者——设定为堕天使。他被逐出天堂,负着一对飞不起的翅膀,掉落秃山,亦是被流放。“没劲”,是他张口第一句断辞,也是整部戏的第一句。
似乎是为了找点乐子,他假称自己是那旅行者,加入此地人事,见识了律法轨辙。在舞台上,收起翅膀的堕天使与敏感善思的新司令官机锋来去,与狂热施刑的军官语焉不详。我们自当不怀疑他的善良,可必须记得他自有矛盾彷徨。“您不信上帝?”他对着这问题冷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教育。看着始终淡漠玩世的堕天使,我不断想起《大话西游》。电影结尾的夕阳下,刺眼昏黄,城墙似矮又高。至尊宝已成为大圣,站在人群中,望着高处的武士与紫霞。他已经历了全部,知晓悔恨与奈何,于是附身于武士,给了她那个吻,给了人间小团圆。
然而我们终究盼不到意中人,亦无七彩祥云。在流放地,除了仍有清稚赤子之心的胖小兵,无人看得到堕天使真身。亦如我们看戏,有所见,有不见,灵魂之选。
所以小兵也只说:看,那个长翅膀的人。
就像大圣离去时,二人对那孤寂的背影笑道:你看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啊。
(作者为小说家,出版有《暴雨下在病房里》《异乡记》等)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