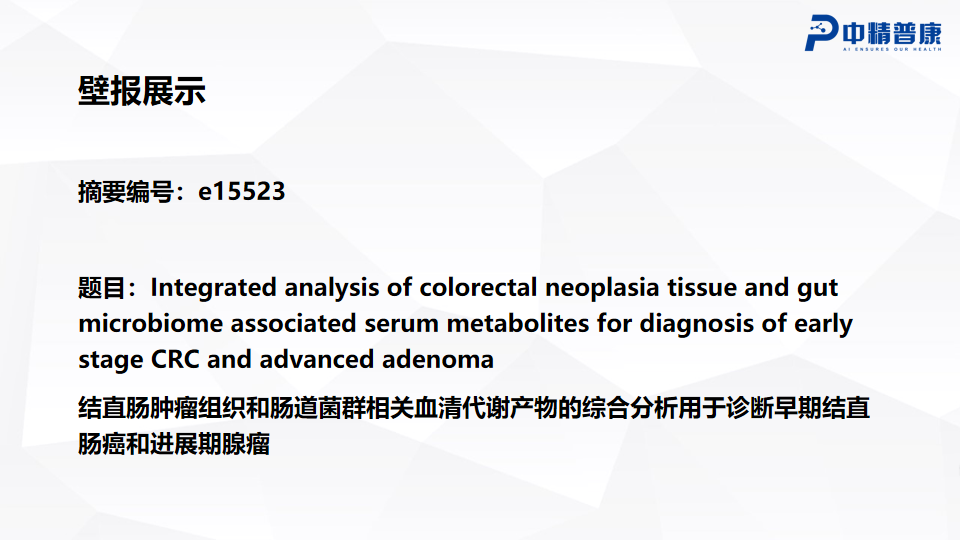《惊梦》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全国首演
11月18日,演艺大世界·2021第七届上海国际喜剧节开幕大戏《惊梦》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全国首演。导演兼主演陈佩斯在60岁时看到编剧毓钺创作的《惊梦》,“一拿到剧本,我就知道《惊梦》是过去没有尝试的戏,像在两座高山之间走钢丝,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又特别享受。”
撕去喜剧标签
陈佩斯与毓钺合作的上一部舞台剧《戏台》演出数百场,每次巡演到上海,依旧一票难求。《戏台》讲京剧戏班,《惊梦》变为昆剧戏班,陈佩斯强调,“故事时代不一样,风格更不一样。《戏台》严格遵循戏剧三一律,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故事特别实在。创作《戏台》,我们像在山脊隆起的小道上晃晃悠悠走,而《惊梦》是翻过山脊的又一个世界,《惊梦》还是‘三一律’,只是分成好几块,时间跨度长到一个月,情节冰火两重天,情绪上上下下起伏,游走在悲喜之间,没那么写实。《惊梦》很早就定了框架,之后我们摸索好几年才找到合适的方法去呈现。”
“《惊梦》喜剧效果一般,故事性很强。”首演在即,67岁的陈佩斯不惮于为《惊梦》撕去喜剧标签,他想探索更多可能,“我们不能为了笑而笑,使劲找包袱,反而丢了故事。《惊梦》演人物、演故事,不像过去那样追求喜剧风格的强化。”
去年年初《惊梦》建组,启动舞台美术设计,由于疫情,排演延迟一年,“我们增加了一年《戏台》巡演,等待《惊梦》首演最佳时机。”陈佩斯说,《惊梦》排练到最后,情节与情绪不再是由演员们控制的,“做《阳台》时,我就发现喜剧有很深的悲情内涵,没有喜剧条件,形成不了悲剧。《惊梦》里有一群人,必须按照他们自己的命运走,偏悲、偏严肃,如果走喜剧方向,可能不够深刻、没有力量。”
虽然陈佩斯给《惊梦》“笑果”打了预防针,但他异常笃定,“我的故事一定能开心好看,《惊梦》会有好票房,我能驾驭这个作品,有一点点炫技。”儿子陈大愚补充,《惊梦》更有诗意,新的风格值得观众寻味。
三代创作者的“争吵”
与陈大愚同台演《惊梦》,陈佩斯直言不讳,父子之间有严重的“代沟”,“我们审美不一样。”陈佩斯要求演员始终面向观众,让大家能看清脸部神情;陈大愚认为,真实是第一重要的事,其次才是让观众看到脸,“演员也可以背对观众释放情绪。”
陈佩斯喜欢现场乐队,“好的表演,无声胜有声,自然声音胜过麦克风扩声。”陈大愚倾向于经过后期打磨的人工音效,“你看《敦刻尔克》,如果没有音乐,什么都不是,情节起承转合都靠音乐铺陈;《沙丘》也是,音乐有美学表述。”陈佩斯立刻反驳,“我们这不是拍电影,戏剧是真实的人与人交流。”
父子俩你来我往,依稀可见排练时的火药味。陈大愚转头看向上海记者,“所以他是导演,我是导演助理。”大家都笑了。

“我和老爹一起搞创作也不自在,常常吵架。”陈佩斯与父亲陈强合作《二子开店》等12部影视剧,“那时我爹经常追着我要下一个剧本,现在儿子追着我要投资。”喜剧人多为能写会演的创作全才。陈大愚曾帮《阳台》改剧本,为《戏台》做场记,三年前拿出了自己写的剧本,以“娱乐至死”为主题,“我有一些想表达的欲望,想鸣不平的东西。现在好多工作室找大学生写稿,润色以后成了编剧自己的作品。”
“他把戏都抢走了”
在更高的价值观层面,比如“应该创作什么样的戏”,陈佩斯与陈大愚又有着绝对共识。几年前,一位外国知名导演在中国推出长达260分钟的先锋派戏剧,陈佩斯看了两个小时后默默退场,“台上有意思,台下更有意思。观众们矜持地相互打招呼,标志着‘我们是一群人’,表达‘我们’在看。”第二天陈大愚也去看了这台戏,观后感接近。
父子俩都关注观众的感受,“创作者得明确自己在做什么。”陈佩斯不像一些艺术家那样高高在上,“我为了生存,得把观众逗乐了,才能活下去,才能养活一个剧团,还能有好日子。”
《惊梦》不是陈大愚与陈佩斯第一次同台。2018年《托儿》第400场纪念演出,父子也曾同台。陈佩斯回忆,“本来没我的事,临时缺个演保安的,剧组怂恿,我就上去了。”
时隔3年,陈大愚清晰记得每个画面,“一开始,我爸遮着脸,观众还没有反应过来,后来他把帽子脱掉,我能感觉到,从观众席第一排开始,大家坐不住了,交头接耳,声浪一层层往后传,是不是陈佩斯?然后我爸喊了一声‘蹲下’,全场笑裂。他把戏都抢走了。”
陈佩斯办了10年喜剧培训班,120多位学生从培训班毕业。如今红火的上海亚洲大厦演艺新空间里,也有他的学生。记者们赞扬他培养了喜剧人才,陈佩斯连连摆手,“别这么说,人家还去中戏学习呢。”
去年陈佩斯完成了关于喜剧理论的书,计划出版,“当下喜剧看着很热闹,其实都能分析出原理。”
《惊梦》之后,陈佩斯下一部戏可能还是与戏班有关,“我就是个戏剧人,所以对戏班的沉浮历史感兴趣,可能是唐朝、汉朝戏班,也可能是秦朝的事。”